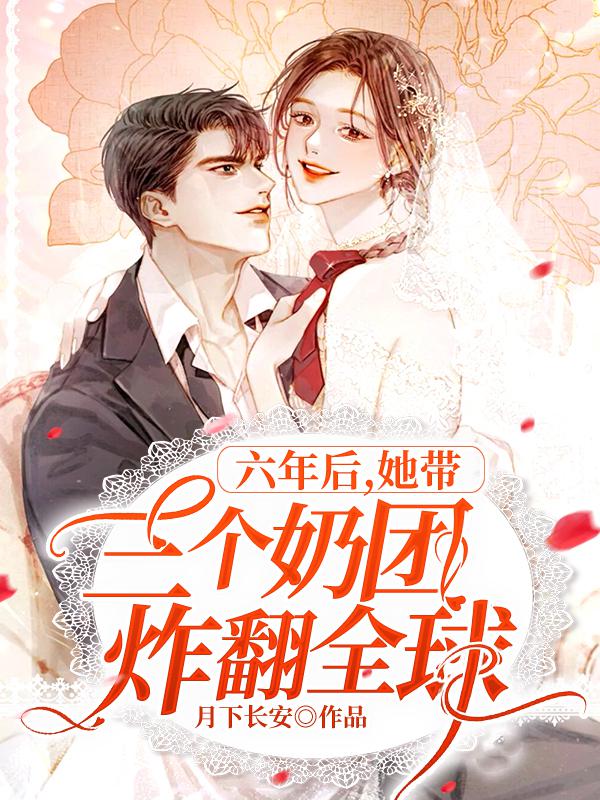第2073章 《掌纹河·卷一:月光下的河床》
记纹村的月光总带着股焦糖味。祠堂后的草田被月光浸得发亮,掌印纹路像银线绣在草叶上,顺着地势往村西的糖窖蜿蜒——那是村里老人说的“掌纹河”,每年秋分后,纹路会亮得能照见水底的石子。
今年的掌印河却有些异样。守田人阿砚凌晨巡田时,发现最老的那片“祖纹区”草叶上,多了些细碎的虫洞,洞里渗着灰黑色的气,沾过黑气的草叶,掌印纹路竟淡了半分。
“是噬天鬼的幼虫在啃食掌纹!”阿柏族长拄着糖木拐杖赶来,拐杖头的“守心”二字被月光照得发烫。他扒开草叶,虫洞边缘的草茎已经发脆,轻轻一碰就断成两截,“它们专吃故事里的‘情丝’,再这样下去,林穗太奶奶的掌印就要被啃没了!”
村里的大人们都慌了。掌印河是记纹村的根,河里沉着百年的故事——林穗与芸婆婆的糖战、阿禾太爷爷的“芝麻解围”、阿枣奶奶的“虫洞补记”,这些故事凝成的情丝,是对抗噬甜鬼的屏障。一旦情丝被啃断,噬甜鬼成虫就会顺着掌印河爬进村里,到时候,别说糖窖里的传心糖,就连孩子们《掌纹录》上的字迹都会被吞得一干二净。
“得补!用新的情丝把虫洞填起来!”阿柏把拐杖往地上一顿,糖木杖点过的地方,草叶竟泛起了浅金色,“按老规矩,‘情丝’得是活人用心熬的——熬糖时想着最真的事,糖浆里就会结出情丝,灌进虫洞,就能把噬甜鬼幼虫闷死在里面!”
消息传遍村子时,天刚蒙蒙亮。糖窖前的核心灶被架了起来,三十口铁锅一字排开,锅沿上还沾着去年冬祭的糖渣。负责熬糖的阿芸(芸婆婆的第五代孙)正往锅里倒麦芽糖,手腕上的银镯子晃得人眼花——那镯子是用当年林穗与芸婆婆的糖模熔了重铸的,刻着两朵交缠的槐花与栗子。
“得用‘同心火’熬!”阿芸的娘在灶膛前添柴,柴火是晒干的记纹草,烧起来带着股甜香,“火里得埋上每个人的头发,这样熬出的糖浆才认亲!”
孩子们也没闲着。阿枣抱着她的《掌纹录》蹲在灶边,把自己扎辫子的红绳拆下来,剪成小段扔进火里:“这绳上有我给太奶奶画的芝麻,情丝肯定够韧!”阿砚则跑回家,翻出他爹临终前用的糖铲——那铲头有个缺口,是当年为了救掉进糖锅的阿禾太爷爷烫的,他把铲头在火上烤得发红,再浸进冷水,“咔嚓”一生,缺口处裂出细小花纹,“这是爹的情丝,比铁还硬!”
糖浆熬到第三炷香时,开始泛出琥珀色。阿芸用长勺舀起一勺,糖丝能拉三尺长,在阳光下闪着七彩的光——那就是情丝。她往糖浆里加了把去年的新芝麻,是阿禾家种的,籽粒饱满,“太爷爷说过,芝麻聚气,能让情丝拧成股!”
等糖浆凉到微温,全村人都拿着竹勺往草田去。阿柏拄着拐杖走在最前,每到一个虫洞,就用拐杖头蘸点糖浆,嘴里念着:“林穗与芸婆婆,较劲不相让,糖锅并排放,甜香绕屋梁……”念一句,阿芸就往洞里灌一勺糖浆,虫洞被烫得“滋滋”响,冒出的黑烟带着股焦糊味——那是噬甜鬼幼虫被闷死的味道。
阿枣负责的是最偏的那片虫洞,那里沉着“虫洞补记”的故事。她往洞里灌糖浆时,突然想起阿柏爷爷说的“错处也能成巧思”,忍不住多念了句:“阿枣画芝麻,歪歪扭扭像小虫,太爷爷说,这叫活着的心意……”话音刚落,糖浆突然“咕嘟”冒了个泡,青丝在月光下结成个小小的芝麻形状,把虫洞堵得严严实实。补完虫洞的第七天,掌印河的纹路亮得吓人。阿砚凌晨巡田时,发现草叶上的掌印竟渗出了蜜珠,滚到地上,凝成了半透明的糖砖,砖上还印着模糊的人影——是林穗与芸婆婆并肩搅糖的样子。
“是情丝结的‘忆糖砖’!”阿柏用拐杖敲了敲,糖砖发出“当当”的脆响,“这是掌印河在谢咱们呢!”
村里把糖砖运回祠堂时,发现每块砖上的人影都不一样:有的是阿禾太爷爷往糖锅扔芝麻,有的是阿枣奶奶补《掌纹录》,还有块最老的砖,上面是两个模糊的小孩,正抢一根糖棍,看衣着,像极了林穗与芸婆婆小时候。
“得把这些砖嵌进祠堂的墙里,”阿芸的娘擦着砖上的蜜珠,“这样风吹雨打都不怕,还能护着祠堂里的《掌纹录》。”
嵌砖那天,村里的石匠特意在墙面上凿了凹槽,每个凹槽旁都刻了故事名。阿枣踮着脚看石匠凿“虫洞补记”的凹槽,突然指着墙缝说:“这里还能嵌块小的!”大家一看,果然有个指节大的缝,阿柏笑着让她把自己熬的第一块“歪芝麻糖”嵌进去:“新故事也得有地方待。”
怪事就出在嵌完砖的当晚。阿砚被一阵“咔哒咔哒”的声吵醒,跑到祠堂一看,月光从窗棂照进来,照在糖砖上,砖里的人影竟活了过来——林穗与芸婆婆在砖里搅糖,糖丝从砖缝里飘出来,落在《掌纹录》上,那些被虫蛀过的空白处,竟自动填上了字迹,比阿枣奶奶补的还生动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