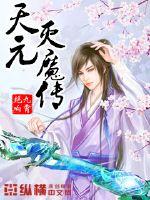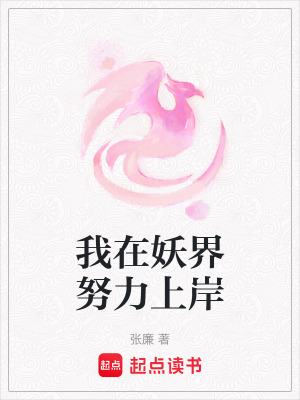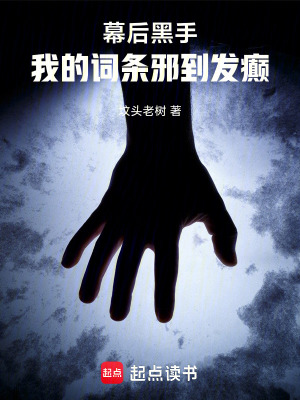六岁那年,奶奶带着我去吊唁一位我不熟悉的老奶奶。
吊唁路上,奶奶叮嘱我:“看见什么都别吱声。”
灵堂里穿寿衣的老人静静坐在亲友中,朝我笑。
回家后奶奶替我擦脸,毛巾突然掉进盆里:“谁让你看她的?!”
我扭头——镜子里,那个奶奶正趴在我背上啃咬着什么。
而真实的尸体……此刻正站在奶奶身后。
---
那年夏天的土路,被太阳烤得像是起了卷儿的牛皮,烫得光脚不敢沾地。
风也是热的,裹着尘土和庄稼叶子腐烂的酸气,一阵阵扑在脸上。
奶奶攥着我的手,攥得很紧,指甲掐得我肉疼。
路太长,我的短腿跟不上,几乎是一路被半拖半拽着往前挪。
“记牢了,”
奶奶的声音干巴巴的,和脚下的土路一个调子。
她没低头看我,眼睛盯着前面望不到头的田埂。
“到了地方,磕头,烧纸,然后就在边上乖乖坐着。看见什么,听见什么,都不准吱声,不准问,记住了没?”
我喘着气,胡乱点头,喉咙里干得冒烟。
为什么要走这么远的路?
去干什么?
那个没了的人是谁?
我全不清楚。
只模糊知道是个奶奶,一个很不熟的、一年到头或许只在年节时远远见上一面的远房姨奶。
因为不熟,所以那点害怕也被漫长的跋涉和燥热磨得麻木了。
路两旁是高高的玉米秆子,绿得发黑,密匝匝地站着,一丝风也透不进。
除了我和奶奶踩起土沫的脚步声,四下里静得吓人,连蝉都不叫。
走到那处院坝时,日头已经歪西。
白惨惨的灵棚搭着,好些人穿着暗色的衣服,聚在一起,声音嗡嗡的,像忽然闯进了一个巨大的蜂巢。
空气里混着劣质烟卷、线香和一种沉闷的、说不出的怪味儿。
奶奶猛地又掐了一下我的手心,压低声音:“刚才路上说的,记死了!”
棺材就停在堂屋正中央,黑黢黢的,一头大,一头小。
我没敢细看,心里发毛,赶紧低下头。
奶奶松了我,挤进那堆嗡嗡说话的大人里去了,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门槛边,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灵堂里很吵,但又让人觉得一种死寂。
大人们三个一群,五个一伙,说着庄稼、收成、家长里短,偶尔夹杂一两声对亡人的唏嘘,很快又会被新的话题扯开。
他们的脸在烟雾里模糊不清。
我缩着脖子,蹭到墙根一条窄板凳上坐下,尽力把自己缩得更小一点。
眼睛只敢盯着自己破了洞的鞋尖。
就在我盯得眼睛发酸的时候,余光里,棺材斜后方,靠墙的那一圈人里,一个身影慢悠悠地晃了进来。
暗蓝色的寿衣,浆洗得发硬,在昏暗的光线下特别扎眼。
银白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稀疏的髻。
一张脸干瘪得像是放皱了的果子,眼皮耷拉着,嘴角却奇怪地向上弯着,挂着一个极其僵硬的、像是用钩子硬扯出来的笑。
是照片摆在棺材头那个相框里的老人。
她就在那堆聊得正起劲的亲戚中间坐下了,安安稳稳的,双手叠放在膝盖上。
她旁边一个穿着灰布衫的男人正大声说着什么旱情,唾沫星子横飞,完全没注意到身边多了个人。
我的血好像一下子冻住了,头皮噼啪地炸开细小的麻。
喉咙被什么东西死死堵住,喊不出,也咽不下。
我想起奶奶路上说的话——“看见什么都别吱声”。
我猛地低下头,把脸埋进膝盖里,浑身控制不住地细细发抖。
我不知道那是谁,不知道那是不是……
可是她明明就该躺在后面那口黑箱子里!
为什么她能坐在那?
为什么别人都看不见?
那个笑……她是不是在对我笑?
我不敢抬头,一秒都不敢。
时间黏糊糊地淌过去,每一息都拉得长长的,折磨人。
耳朵里灌满了那些无关痛痒的闲聊和那个灰布衫男人粗嘎的笑声,混合着我自己心脏咚咚捶打胸口的巨响。
后来,奶奶过来拎起我,说该回家了。
我像个木偶似的被她牵着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外走。
跨出院门那一刻,我几乎要瘫软下去。
直到走出老远,拐上了田埂,我才敢偷偷回头望。
那处办丧事的院子已经变小了,模糊在夕阳的光尘里。什么都没有。
回去的路感觉短了些,也许是我只顾着埋头走,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那个穿着寿衣坐在人堆里的影子,还有那个怪笑。
天擦黑的时候,我们进了自家院门。
煤油灯已经点起来了,昏黄的光晕撑开一小团黑暗,灶房里飘出晚饭的香气。
熟悉的、令人心安的味道。
我僵硬的四肢终于慢慢软和过来。
奶奶打来一盆温水,浸湿了毛巾,拧得半干,给我擦脸。
温热的毛巾敷在脸上,很舒服,我闭上眼,长长地、劫后余生般地吁出一口气。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